2016年1月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在守静活动日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学习讨论。首先是陈建桦博士主讲,对这个规定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然后守静律所的律师对规定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主讲内容:
谢谢主持人袁媛律师和各位律师提供机会让我针对这个规定做发言,下面简要从三方面谈下我的看法:第一是制定背景及内容概述;第二是对规定亮点及不足的分析;第三是完善规定的应有态度。
一、制定背景及内容概述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规定”)的标题可以看出是对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的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的进一步细化深耕,也可以从规定看出我国立法部门及司法部门的一些态度与立场。
1.制定背景
第一、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重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不只是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更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裁判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我国的司法现状,一些法官对辩护律师的态度并不如对公诉人的态度那么“友好”,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没有很好地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若要更好履行其职责,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对辩护律师进行了必要的诉讼武装,才能让辩护人与公诉人之间实现良性的制衡。因此,“最高法规定”的出台彰显着有关部门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的重视。
第二、突显了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角色的特殊性。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是居中裁判的,应当价值中立地行使其审判权,这是众所周知的。虽然,随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会出台自己的相关规定,但是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最早或者“最积极”地发布“最高法规定”呢?某种程度上可以从法院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角色看出,法院与律师之间没有直接的对抗制衡,民事诉讼自不待言,刑事诉讼同样如此。因此,许多对于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制度改革或者完善,法院往往会比公检两家更加“积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检察院天然的角色不可能积极地去推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刑事司法改革中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都不会由检察院带头。
2.内容概述
首先是标题措辞上的表达,可以看出“最高法规定”的标题强调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主体对律师诉讼权利的落实,保障应当达到“切实”的程度,对律师权利的保障也在标题上强调了对象是诉讼权利。
其次是对现有保障律师诉讼权利规定的排列组合以及一些细化。具体来说,“最高法规定”有十条,每条都是对一项具体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内容原来是散见在各个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之上,这些规定大部分内容其实是对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律师诉讼权利的再次排列组合。当然,这些规定也有对现有规定较为模糊部分的一些明晰化,或者宽泛规定的细化。比如第三条对实习律师参加诉讼内容的细化规定。
二、规定的亮点及不足
1.规定的亮点
亮点部分主要是对律师知情权保障的简要评价。包括理论界、实务界以及舆论各方对律师知情权的强调已经非常详实,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主要从我参加的一个会议的内容侧面彰显“律师知情权保障”。上个月,我有幸参加主题为“法治建设中的立法及司法公开”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主办方是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法研究中心、深圳市律协和英中协会,会议的内容从主题可以看出是对立法及司法公开相关内容的讨论,其中印象很深也与这个规定契合的是,来自最高法和最高检的相关负责人强调会重视对诉讼律师知情权的保障,便是通过司法公开的方式实现。这些方式不再是传统的、被动地公开,而是主动的多渠道地公开,而且特别强调会利用目前的互联网技术。会议上,最高法法官与最高检的检察官在与深圳律师代表讨论的比较多的也是如何保障律师知情权的问题,“最高法”规定本身便是对司法机关态度的最好彰显,自然是重要亮点。
2.规定的不足
作为负责任的法律人不能仅仅点赞,应当根据现有的司法环境提出不激不随的观点,特别是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一、创新不足,细化不够。我认为不管是“最高法规定”,还是去年颁布的“两高三部规定”,其实更多地是一种宣示性的规定,没有足够的实质创新。虽然从立法权限来分析,司法解释本身没有权限立法,只能对现有规定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行填补。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细化是不足的,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更多的只是排列组合。
第二、可操作性不强。规定本身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相关的立法部门对于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重视,但是这些保障并没有对操作问题进一步明确。作为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本身的价值就是对于法典无法详实规定的内容的明晰化,但是从“最高法规定”来看,还是过于空泛。
第三、规定并不科学。法理上说,法律规定本身如果没有惩罚性的内容,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没有实质的威慑力。换言之,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司法机关如果没有做到规定所要求的“应当”等内容的话,将受到怎样的“惩罚”,这没有在规定上有体现,这样的立法安排,如果不是故意为之的话,立法科学性上也是存在问题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苛责”这个“最高法规定”,因为法典都没有规定这种惩罚性措施,作为补充角色的规范性文件是没办法越俎代庖的。
三、完善规定的应有态度
按照一般的套路,提出了1,2,3点不足的分析,应当对立法部门或者司法部门针对性地提出谏言。在此,我也会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只不过建议的对象是提出批判观点的人,或者催促即刻完善的人。不提出立法完善意见,除了因为水平有限,不敢越俎代庖,相信研究律师权利保障主题的专家会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更关键的原因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难度。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各部门的利益以及资源的博弈和权衡。陈卫东教授在课上和课下,不只一次和我们强调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难度只比宪法低,需要很高的智慧。主要观点是刑事诉讼法涉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资源的权衡和博弈。因为改动某个条文的某项内容,便是涉及公检法三家,特别是公检两家的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这种分配并不是政法委或者某个部门可以统筹协调的。比如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限的问题便是典型的例子。全程参与1996年第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陈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在几年的学习和实践中我越发赞同陈老师这一观点,因为一般的财产利益博弈都需要权衡各方,更不用说博弈的主体是最高司法机关,博弈的对象是关乎公民人身权利的刑事司法权限。
第二、我国目前的理念有两极化的倾向,增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难度。法学专业人士或者其他相关人士呼吁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应当不断向西方先进法治国家学习,更加注重对于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但是,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却不这么认为,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很了解,就不展开了。
第三、我国各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环境不一,甚至在一些方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制定过于细化的规定是否可行。或许应当呼吁提高省级人大,甚至是市级人大的立法权限可能是更好地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在呼吁完善规定的同时,也应保持必要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是对现实的妥协,更不是和稀泥,而是对法治之花绽放的必要等待。
由于仓促准备,不妥之处,望海涵指正!
点评内容:
我赞同以上两位的观点,我主要是根据自己办案的经验谈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中关于知情权的问题。实践中,如刑事案件,办案机关时常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情况,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情况未及时告知辩护律师。未能确实有效的保障律师的相关权利。这些问题其实正是建桦所提到的规定自身并没有具体细化的问题,而这种细化是亟待解决的。
袁媛律师(守静副主任、合伙人):
上面都在谈论“最高法规定”的不足之处,我这里谈下“最高法规定”的亮点。即“最高法规定”第四条,明确了除了律师发言过于重复、与案件无关,或者相关问题已在庭前达成一致等三种情况外,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不应打断律师发言。这一规定通过列举的形式进一步保证了律师的辩护权,结合本人之前在法院工作时参加庭审的经验,应该可以很好的对法官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进行约束,是本《规定》的亮点之一。
刁林丰律师:
同意袁律师的观点,但觉得要完全落实这条规定,不仅需要进一步的实施细则(规定法官违反该规定侵犯律师辩护权的法律后果),更需要法官庭审理念的更新。否则,规定就仍然停留在纸面不能落地。
李月新律师(法学硕士):
对于“最高法规定”我主要谈下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关于第四条保障律师辩论、辩护权:如何体现“合理分配诉讼各方的时间”,现实庭审中律师发问、发表辩护意见的时间不能切实保证。
第二、关于第七条保障律师的人身安全:对比15年9月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明确具体可采取的保护措施。依何法,如何处置。
第三、关于第十条救济机制:对投诉的如何调查、如何处理应简要明确。对比本人之前在检察院、法院的工作经历,现行规定更为全面的保障辩护律师的各项权利,有利于辩护律师及时依法、依规行使辩护权,最大化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刘珊珊律师:
我主要补充谈下“最高法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观点,这条规定了依法保障律师的人身安全,对律师的人身安全保障纳入明文规定,有利于引起地方法院的高度重视并有助于法官贯彻落实。因为目前实践中,有的案件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对律师进行侮辱、诽谤,但法官并未及时制止当事人,律师的权益受到侵害,而庭审也无法继续进行。
田鹏(刑诉法硕士):
我谈下“最高法规定”第五条关于保障律师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的观点,这一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至102条的细化落实。换句话说:只要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1辩护律师申请2提供相关线索3法官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不论辩护律师在开庭审理前提出还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法官“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或进行法庭调查,经调查确认存在法律规定的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而本条文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有所突破,换句话说,本条文依然是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的言辞类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实物类证据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才排除的缩影。如此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为司法机关预留了裁量空间,实质是限缩了律师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对于该条文,应该从立法实质解释的角度,对于“3个法定条件”作出具体明确的细化规定,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权。
王育平顾问(前任资深法官,守静首席专家顾问):
我赞同你的观点,“最高法规定”有亮点,也有不足。我这里主要对“最高法规定”第六条中关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定谈谈看法。毫无疑问,这应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的规定来理解,目前关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规定有《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条一第53条和《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等。应该说,“最高法规定”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协助辩护人调取证据的刚性职责和义务,是“应当”。且我认为还扩大了调取证据的范围,因为原来的相关规定只是针对公安检察机关未移送的材料,以及针对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被害人或者近亲属等不同意的情形,而新规定只要求符合法定条件即可申请法院调取辩护人认为需要调取的证据材料,应当包括言词证据、书证、物证、电子证据等。主要问题是并没有明确“法定条件”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就是刑诉法解释第53条规定的内容即可?从立法论的角度以及有利于贯彻实施来看,有必要对这个规定进一步明确具体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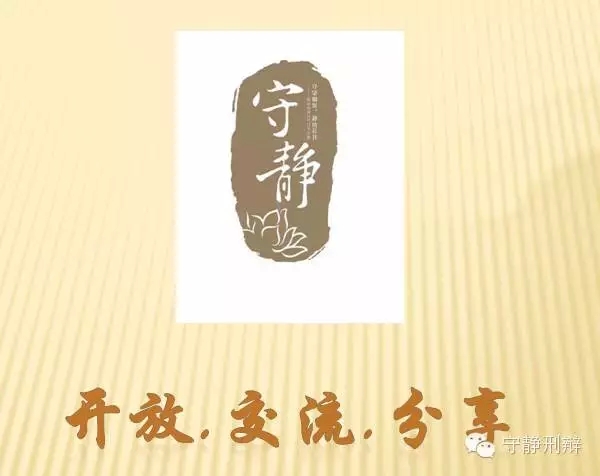
守静律师:守望刑辩,静待花开。



